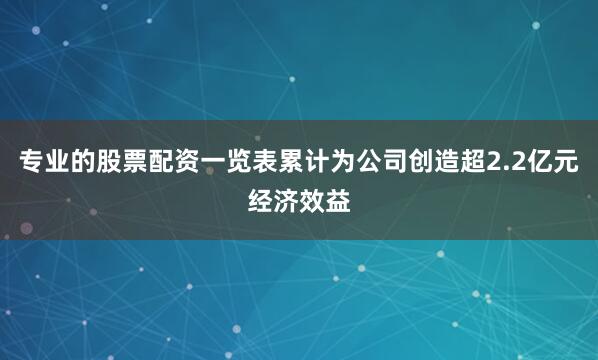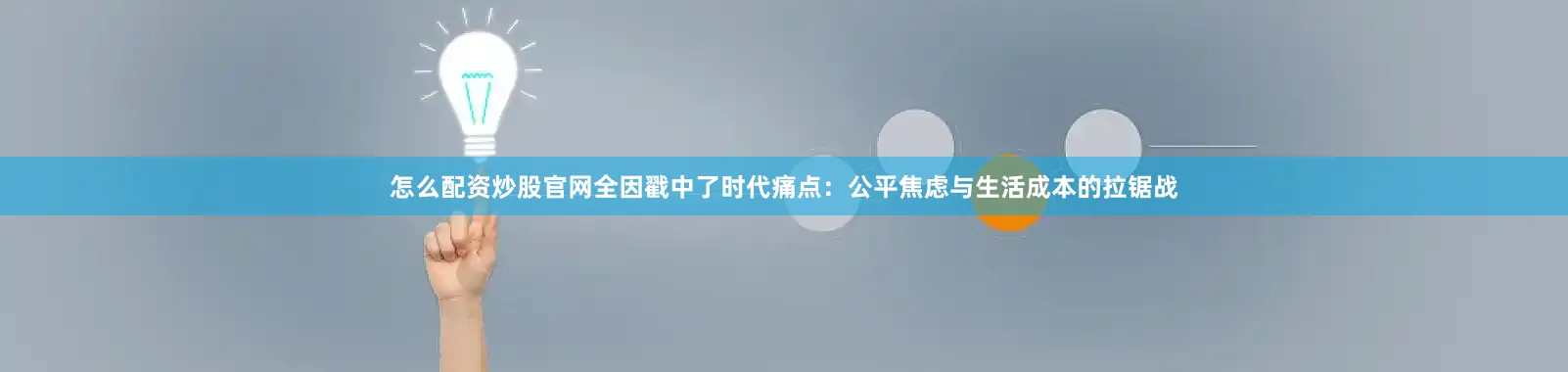开封的水,决定了刀兵的路
五代的城池,常因水路兴衰。等到汴梁成为北宋东京,人们只记住了“市列珠玑,户盈罗绮”的繁华,却很少回头看是谁把河渠打通、把航线铺平。柴荣登位后,拿着地图在淮安城西一带来回勘察,盯上的不是城墙,而是河道。他看到邗沟前方一道堰域横拦如石门,巨舰过不去,水军便如被掐住喉咙。沿着淮河边的鹳水走了一圈,他想到绕行——把这条与邗沟相连的支水加宽疏通,避开障碍。大臣们以地形复杂、工程难度高为由摇头,他却没有退缩。不到半个月,鹳水拓通,后周数百艘巨舰由此直入邗沟,最后抵达长江。南唐措手不及,《资治通鉴?卷二百九十四》记下当地人的惊惶:“唐人大惊,以为神。”
如果将战场视作刀尖,后勤便是刀背。柴荣不满足于一条捷径。他继续整治汴河,开封城周围的运河也陆续修成。蔡水向东南连颍水入淮,五丈渠由开封直达梁山泊,再通山东半岛,这两条水线极具战术价值。沿蔡水行军,后周可以在淮南西路开辟第二战场,直取寿州、濠州、滁州,还能以舟运源源不断地送去攻城器械与粮草;顺着五丈渠,禁军乘船快速抵达山东,既能平息地方兵乱,又能提防契丹从渤海湾南下。水利是一张缓缓展开的巨网,战争不过是网中抓取的一次。
展开剩余85%兵贵精,不贵多
水路通畅只是长远之计,兵的质量才是战场上的当下。柴荣即位时亲自带兵,第一眼看到的,不是敌军的锋芒,而是己阵的散乱:将领有令不行、士卒畏敌怯战,阵线一触即溃。禁军内部的层次更让人心惊——少年扛不动兵器,耄耋走不动路;有的人身强体壮,能拉得满弓、扎得住营;有的人力气小到连弓弦都无法上。数量看似庞大,能上阵的却不及半数。更现实的压力在民间,一个士兵往往要靠一户甚至好几户农民供养,这样的冗兵制度,只会拖空国力。
他不愿再被“人多即强”的幻象裹挟。改革从筛人开始:武艺好、体魄壮的军士一律往上提,那些不达标的,干脆遣返乡里务农。这个取舍在当时并不好做,因为舆论惯性总倾向于“练兵不如募兵、增兵不如添兵”,但他强行拧转方向,还派赵匡胤去各地择才,将选中的人编入“殿前诸班”。殿前司是京师禁军的核心,一旦把各地精锐吸纳于此,军令传达、训练节奏与作战标准便能统一起来。效果来得很快,《资治通鉴?卷第二百九十二》不吝评语:“由是士卒精强,近代无比,征伐四方,所向皆捷,选练之力也。”与其在帐簿上堆数字,不如把刀刃磨亮;这在柴荣这里,不是口号,而是行事准则。
皇帝站到前线,是承担,也是判断
五代乱局里,亲征的皇帝不算少,但能真正扭转局面者并不多。危险显而易见——一旦战败,国本动摇,甚至引来诸侯乘势而起。柴荣仍选择把自己置于第一线,背后却不是莽撞,而是对改革后军队成色的把握。他知道,将领能统一调度、士卒不怯战,下面的队列才会在关键时刻稳得住。
他把几场战事当作试卷,逐题作答,顺序并不照着别人的棋路走。针对南唐,他接连出兵,从那一年起到显德五年止,三次亲征,目标只有一个:把长江以北的淮南地区收归后周。地盘一寸寸推进,逼着一直自居“正统”的南唐李氏抛下身段。南唐并非不善战,只是被水路奇兵与精练禁军双重压制,后劲渐失。
而在北线,他将矛头伸向契丹。显德六年那次北上,仅用一个半月便连取三关、三州、十七县,几乎把燕云十六州之门掀开到门槛。燕云之地在五代就是硬核战略资源,谁拿住,谁就能握住北方的咽喉。这种推进速度,在当时的诸侯之间确实罕见。比起单一的子弹压制,这更像一整套方法论在起效:选练新军保持攻坚力,水路后勤提供持续性,前线指挥稳住节奏,地方治理不致崩盘。
向西的试探也没落下。显德二年,他发兵后蜀,未能根绝其国,却把秦州、成州、阶州与凤州这几处在中原战乱中被后蜀占去的地盘收回。这种“收边打磨”的举措,常被人低估,但恰恰是稳疆的要点:你不必每次都一口吞下对手,只要把关键的、能连接你战略纵深的州郡拿回,敌方的大势就会被迫改线。
至于起手的第一场硬仗,是显德元年的泽州会战。北汉与契丹联军南下,后周的首都风声紧促。他御驾亲征,于泽州(今山西晋城高平一带)率兵硬拦,拿下大捷,也使后来诸军出动时有了信心积累。高平之战的意义,不仅在结果,更在于用真实战况核验改革效力——将领能否依令而动,士兵能否稳得住心、撑得住阵,胜负就在这种细微的“纪律成本”上分出。
水与兵的互哺,是他真正的战略
把几场战事拆开似乎只是皇帝的胆识与将帅的谋略。但把水利和军制放在同一张桌面上,就能看到柴荣的布局是互相牵引的。汴河长期失养,开封与外界的沟通像是被堵塞的血管。他即位后持续进行河道清淤与堤岸修复,外加新运河建设,把京师周边的水系织密。然后动手改邗沟、疏鹳水,再整治蔡水与五丈渠,把通江达海与联通山东两条线打通。河的路线变了,军队的行动方式也随之变化。过去运械靠人挑马驮,速度慢、耗损大;现在一船当百车,攻城器具与粮草成批出动,战线的“渴”被治好,士气自然不散。南唐之所以在淮南北岸节节后退,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这套水路后勤打乱了节拍。
他不是只会修河的工部尚书。柴荣读过“善为国者,必先除其五害”的旧文,管仲的建议里,“请除五害之说,以水为始”,把水害放在首位。把这句话拿来指导国家,便有了一个简单却有效的逻辑:治理水患是民生,疏通运河是后勤,两者合在一起就是战争的底盘。把底盘打实,战术才有腾挪空间。
与“官员好看数字”的观念拉开距离
与他同时期,不少官员仍着迷于兵员报表上的“总数”。这种心态其实容易理解:在权力结构中,数字看上去最有安全感。但柴荣从战场的失败里嗅到另一种味道——数字堆出来的是规模,不是战力。禁军混入大量不堪一用的兵,既拖累训练,也拉低士气,还让民间供养陷入疲敝。他的决断是反直觉的:宁愿减少编制,也要提高“有用之兵”的比率。这一刀切下去,军队的平均水平就被迫提升,纪律和执行也会随之一致。
而让赵匡胤各地择人并入“殿前诸班”,等于把精英置于一个统一的指挥体系里。殿前司作为禁军中最精锐的部分,一次次在战场上扛下攻坚任务,前线与中枢之间的信号传递不再被耗散,战机也不容易被在途消磨。与此对比,南唐的防线更多依赖既有地理阻隔,后蜀则寄望于山区地形与远距缓冲。对手们当然不会轻易崩溃,但当后周把“精兵+水路”的双钥匙插入锁孔,局势便不可逆地倾斜。
制度的细节,决定了结局的可能性
把一名士兵放回乡里不是宽仁,是精算;把运河修到能通巨舰不是铺张,是战略。后周的几次大战因此有了不同的“底气”:显德元年的高平之胜,斩断北汉与契丹联军的南下势头;显德二年的西进,收回秦州、成州、阶州、凤州;此后至显德五年,三次压向南唐,握住淮南北岸,使李氏不得不臣服;显德六年的北伐,以一个半月之速取三关、三州、十七县,差一点就把燕云十六州扳回。数字并排着更能显出步伐的紧凑与方法的一致。
人们习惯从“胜仗”寻找英雄感,但柴荣的厉害在于把看不见的工程和看得见的军功编织成一体。军队精了才能打,河道通了才能稳,民生稳了才能养兵,三者互相回哺,才有了向外推进的常态能力。开封后来之所以承载北宋的都城功能,从某种意义上说,是沿着他修过的水把粮和人送到了城心。讲“东京梦华”的人多,提到邗沟改线、鹳水拓通的人少;可历史的繁华向来建立于某个不起眼的工地与堤岸之上。
若时间再宽一点
历史向来会留白。若他能再活几年,燕云十六州的归属未可知;至少从显德六年的推进这不是一个只写在诏书上的愿望。他已经把禁军的骨干磨出来,把水路的网织起来,把战场上的节奏抓住。后来的北宋在开封合拢市井、经营漕运,也得感谢前朝的这层底子。人们说“选练之力”,说“以水为始”,这些话放在纸上很轻,在现实里却是反复掂量、反复试错的路。柴荣做的,恰恰是把那些看似琐碎的环节连成线,再把线织成面,于是战争不再只是冒险,治理也不再只是善意。
他把兵与水、胜与守,拉到同一个秤盘上,等待的是一个更稳的未来。历史只给了他短短几年,他却把很长的影响留给了后来的人。
发布于:江西省天载配资-国内股票配资-炒股杠杆网站-配资查询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全国股票配资公司排名出炉展开剩余68%得益于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快速发展
- 下一篇:没有了